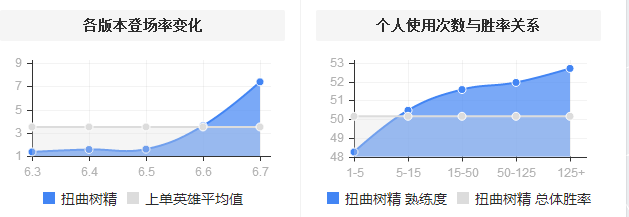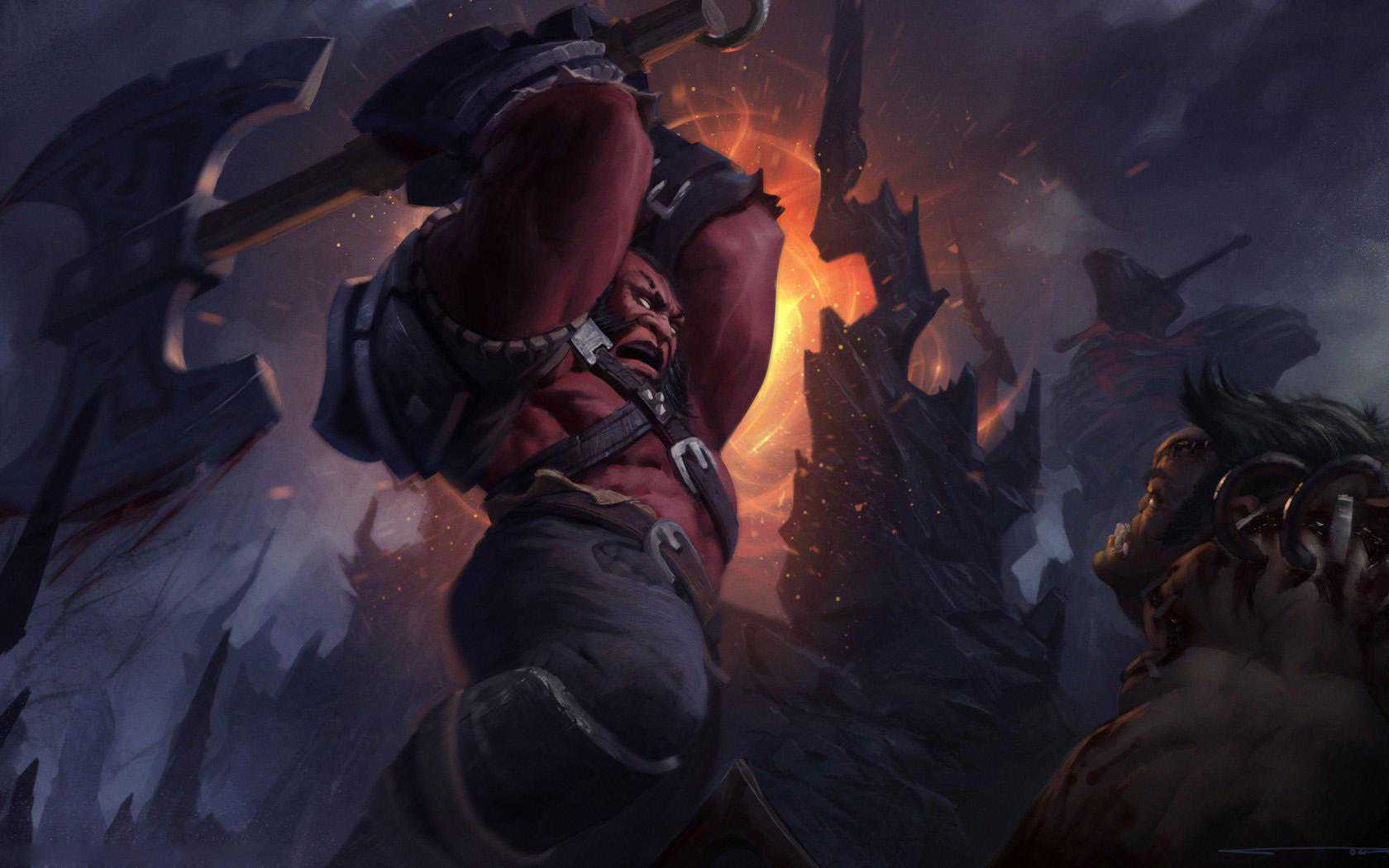远逝的鸽子
刘希国
扑棱着或白或灰或酱紫色的翅膀,稍稍绕一圈,然后飞至楼顶外围装饰的花式小廊檐处,呢呢咕咕诉说着家事或情话。这些小精灵,一年四季像忠诚的侍卫守护着这座楼房。
此前,鸽子栖息的楼房处在东西主干道和南北巷道交汇的东北角。南面是车流,手扶子喊破嗓门似的嚎叫着,小汽车蛮横地疾驰而过,现在路上又多了一种走起路来颤颤巍巍的电马子。南北的巷道永远充斥着污水与秽物,鸽子却依旧不离不弃。朝暾升起的时刻,鸽子成群结队飞起,绕楼顶飞速盘旋俯冲一圈,似在做短暂的告别。倏然间便飞得无影无踪,它们是去完成某项生命的约定,还是去到遥远无忧的地方觅食?是自觉地远离工作的人们,不使他们受到烦扰,还是永远翱翔于冥空,保持飞跃的姿势与活力?一切都无从知晓。当人们清晨还在系鞋时,鸽子早已飞跃千楼万林,脱离了人们愤恨攫取的视线。
我工作的地方在县城东圃。每天要从这座楼下路过。还能看到几只鸽子在练习翻腾的动作,或在锻炼滑翔的技能。有几只蹲在狭窄的台边上,冷静地注视着地面蠕动的芸芸众生,一动不动,像个深刻冷峻的哲人。让人心生烦意的是地面台阶上到处是灰灰白白的鸽粪,厚厚的样子。一个中年男子,穿一条蓝色大褂,持一柄长头扫帚,卖力地打扫鸽粪,脸上浸满了杀气、无奈。扫完之后,拿个簸箕,将鸽粪铲入旁边破烂古旧的垃圾箱,悻悻地转身离去。有时,男子抬头向上一翻眼,嘴里恨恨地“哼”一声,转身进了公司后院。我心里想,弄一袋子去当花费,一定会枝繁叶茂。
有时,从楼下经过,天上会有碎木屑或粪末儿飘落下来。抬眼望去,鸽子来来飞飞,相互打着招呼,仿佛忙忙碌碌的样子。鸽子开始做窝,伟大的育子活动就此拉开帷幕。楼的外面是欧式装饰,越往上走,一层一层的台边匀称而舒适。我想,在“豪华大套房里”,鸽子一定很舒适的,幸福指数一定会很高。晚上值班结束回去时,能听到鸽子幸福自豪的“咕咕”声。放眼看,一层一层的鸽子整齐地站着,机警地注视着楼下的一切。为了驱赶鸽子,楼墙上安装了惊吓飞鸟的装置,但无论怎样恐吓,鸽子从当初的一阵惊悸到现在的从容镇定,它们冷漠的眼光便是对自以为高明的人的嘲笑。
日子在仰高俯低、车来人往中逝过。
生命始于脆弱,终于强韧。一天中午,上班从十字路口的这座楼下经过,远远就看见几只鸽子躺在地上,身子已僵硬冰冷,两眼似闭非闭,侧卧着身子,爪子半蜷,蓝灰色的翎羽有些混乱,身子下是杂沓的鸽粪。一共四只,我有点惊悸。才过楼角,又是两只躺卧地上。它们从楼顶坠落至地,该有多疼啊!是受到了夜猫子的攻击,还是受到了自己赖以依靠的人类的暗算,还是不幸染上了重疾?总之,从半空绝望坠落,飘飞的精灵以一种怎样的状态面对死亡的威胁,让人不得而知。我不忍久视,快速离开了这里。
有时,看到成群的鸽子衔枝垒窝,心里轻快许多。鸽子栖息的台边外部有玲珑小巧的护栏,安全系数倒是提高了不少。但鸽子就是太执着了,太死心眼了。不知道提防。不像燕子,春暖花开时节,正当人们念叨燕子怎么不来了时,仿佛骤临的春雨,燕子“唧唧唧”地飘然而至。燕子也衔草垒窝,不时有秽物洒落,在引起人们的怨恨时,燕子又悄然而逝,不让人厌烦记恨到骨子里。鸽子就是忠诚的卫士,日夜守卫在这座楼顶上,台边上,不离不弃。当然最让人生厌的是那一层一层灰灰白白的鸽粪。
人类最直接的伤害就是釜底抽薪。于是工程队来了,搭好梯架,把鸽子栖身的台阶、护栏等全部敲碎,然后在光溜溜的水泥墙上又贴上了瓷砖,鸽子的“空中花园”永远定格在记忆中。
此后,经过这里时,还有几只恋家的鸽子扑棱着翅膀,落在楼顶的边沿上,无助地望着芸芸众生。鸽子心中一定充满了疑惑。但它们不知道,人们把它们当做和平的象征时,一定忽略了楼下台阶上的灰灰白白的鸽粪。
清晨,倚窗南望。祁连雪峰云岚弥漫,苍崖铁树依旧清晰。还能看到那座楼上有零星的鸽子旋飞旋落。鸽子热热闹闹的场景也永远沉淀在我记忆的星空里了。
别了,我的鸽子!别了,飞翔的精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