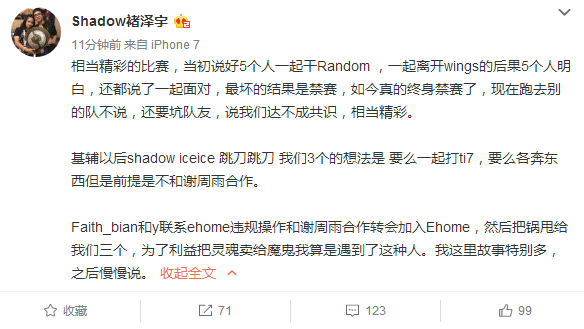李向成憋着一肚子火气回到团防局,当面指着邓韶清的鼻子恶声恶语臭骂起来:“你家里人的眼睛是藏在裤裆里的吗?为什么没看清楚就来瞎说?真该欠揍!”
邓韶清实感冤屈。他拍着胸脯说:“我敢对天发誓,我家里的人的眼睛不瞎。吴太贞那小子就是进到夹沟集里来了。窦宜敏学业深厚、机敏过人,这些人来到他家里他不会不提防的。总爷,若想抓住这几个共党分子还为时不晚。眼下你只需把团丁派出去……说着,他在李向成面前轻声叽咕一通之后,又重重拍着胸脯说,若这一次是我说的话落了空,我甘愿头朝下走上三圈给你看。
李向成很是不以为然,连连摇着手说:“罢、罢,你就是头朝下走上八圈也没人给你喝彩。今儿咱们来亮的,若是你的计谋落了空,就给团里这一、二百号弟兄每人来一双新鞋新袜。这一次你敢不敢跟我赌?”
“成。我邓韶清决不装孬!”
邓韶清为清末秀才。科举废除后,他在家里专门研读刑典野史,并留心窥测、探寻世人心态和泼赖行为。最后,演习练就出写诉状、呈子的本事。纸面上,文笔老辣,刺骨带血。凡是经过他手书代笔的状纸多为胜者。自此,乡间百姓称之为“铁笔御史”。士农工商对其多敬而远之。此人本是一色鬼,对待女性,一不论年岁大小,二不论长辈的婶姨姑表、和免辈的内外侄女,只要肤色容颜被其看中,他非要百计千方弄到手里奸污不可。为此,世面上皆称之为“淫狗”。平日里他为别人写状子,不光银钱要得多,另外还要带他去城里逛妓院。为了满足其兽欲,他曾不知羞耻地公开扬言:对女人,除去生我者、我生者之外,可一概为我所享受。本来,他的大儿子精明强干,做事极有章法。结婚后却变得疯疯癞癞、傻气十足。二儿子聪颖绝顶,读书一目十行。没料到娶亲后,竟变得木纳、呆愣,无药可治。两年前,他的小儿子新婚燕尔不足一个月,就被他支派去南方讨要一笔陈年老账去了。当天夜里,他就拨开新房的门闩,把小儿媳妇给奸污了。第二天早晨,小儿媳来到婆婆面前磕头请安时,忽地打怀里拔出一把锋利的剪刀来,欲要在婆婆面前自刎。说老公公是狗不是人。今天,除非他跪在我面前磕头赔礼,并当众声明今后再也不干这种出格的下流行为,我才跟他罢休。十分奇怪的是,婆婆听罢,一没有惊慌失措,二没有上前劝阻,竟然格格一笑,说,进得我家的门就是我家的人,是我家里的人就要随我家的规矩。你说的这些,全是男女性事,见怪不怪。往后,你就忍下来吧。小儿媳咋也咽不下这口气儿,私下里她决定去找大嫂、二嫂评理并寻求帮助。毕竟她俩人是先她跨过这道门坎的。没想到两位嫂嫂听罢以后竟神态坦然,不仅不去抚慰她极度伤痛的心灵,也不去回答她应该去作何种处置,而是张口吐出刺心锥肺的话儿:我俩个相貌丒陋,体胖肉厚,自然得不到公公临幸欢心,我们倒想问问你是用的什么法儿勾引住公公的魂儿,受到宠幸的?两位嫂嫂的这一计反巴掌直打得她晕头转向。顿时,她脸烧心跳,急急掩面跑回自己房间里去了。夜间,房门再次被推开,小儿媳知道又是那个老不死的进来了。她把手悄悄伸进忱头下,抓过那把刃口锋快的剪刀,牢牢握在手中。她暗中决定,一旦那个老扒灰头钻进她的被窝里时,就用剪刀狠狠扎进他的胸口,要不,趁势剪断他的坏根也行。白天她四处求援,无人同情更无人肯伸手帮忙。她一个刚过门的新人实在是没有勇气向外张扬,她要死死维护自己的那份尊严,毕竟结婚还不足一个月,通体亮丽的新人绝不能让猪狗朝身上泼污水。她左思右想只有用这个绝法儿来得爽当。杀死他以后,世面上的人一定会赞扬我做得对。
房内一时静得令人心颤,那个该死的老东西并没有像昨天夜里那样如狗抢骨头似的急切莽撞上床来,他只是在床前的空地上,像毛驴拉石磨那样一圈圈转悠起来,嘴里轻声表白:媳妇呀,你别怪我当公公的不吃粮食成心干扒灰的丒事。我这是可怜你呀。怕你在新婚蜜月里就空床守单。这可是大不吉利的坏事呀。可恨我的小儿子娶了你这么个百不挑一的俊俏媳妇却不疼不爱,他是舍不得自己的小姘头呀。被窝里的小媳妇急急询问:爹,他外头有人?公公重重哀叹一声:家丑不可外扬呀,原以为给他娶上媳妇后,他总该能改邪归正了吧。没料想,不出一个月他又旧病复发,借故去找自己的老相好的去了。我当公爹的为了团住你的心留住你的身,只好干这宗丟人现眼的丒事。缩在被子里的新媳妇忽然莹莹哭起来。是念叨自已命运不及,是怪爹娘糊里糊凃把她推到这个火坑里,还是要感谢公爹大义为人的举止,她一时说不清楚。只管任性哭下去,好一阵子方才打住。公爹说事己至此,你自己要多保重才是。万万不可胡思乱想,年纪轻轻的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呐。说罢,他转身走开,并殷殷叮嘱她把房门闩牢实,有事儿就喊一声。小儿媳妇没有再犹豫,说公爹,你还是在儿陪着我吧,有你在我心里踏实。邓韶清说:你说这话不假。老辈人哪有不疼爱少小的道理?自然你有心留下我我也就不推辞了。只是你要把手里的剪刀丟开,要不,它会硌人的身子骨呀。随着铛郎一声剪刀落地后,邓韶清便一个猛虎跳涧,扑到小儿媳的床上,说小乖乖,这就怪不得我干扒灰的事儿了。
小儿子在南方讨债时,因欠债人一时凑不足钱款,只好多呆了几天。回家后,便把钱款如数交给爹爹。这才一头扎进喜气洋溢的新房里,再也不肯露面。可是,新婚的妻子并没有显露短暂离别后的欢欣,却甩出一副令丈夫十分沮丧的冷腔冷调。他哪肯罢休?一番穷追不舍后妻子才慢慢道出实情。登时,这小儿子像遭到五雷击顶似的,瞬间变得呆傻怔愣起来。足足过了一个时辰,他哇地一声吐出一口鲜血来,喊叫一声猪狗不如的东西!一头栽倒在地上昏迷不醒。前后不足两个月便撒手归天了。
刚把小儿子送下地以后,没过三天,邓韶清又堂而皇之摸到小儿媳的房子里尽情寻欢逍遥去了。其间,他郑重许诺:河岸那八亩旱涝保收的田地就划归你娘家的门下了。从此,那个小他三十多岁的小儿媳妇就被他毫无顾及地揽在自己的怀抱里来了。
团总李向成按照邓韶清的谋划把巡夜的团丁分成两队,一队守在北门外的夹栏河岸边,这儿是吴太贞回家的必经之路。一队埋伏在夹沟集西南的四里桥附近,为的是防备窦宜敏舍近求远故意兜圈子。有这两道关口把守,准能够把逃走的共党分子逮个正着。
自认为己经撒开天逻地网的“铁笔御史”,立志要用此事去报复六年前窝在心中的私仇。那是他头一次跟窦宜敏在县衙大堂上交手,结果就被他斗得狼狈不堪。
当时,一个名叫梅老五的光棍汉在邓家扛长活己经干了三年多,因邓韶清平日待人刻薄,当长工的连饭也不能吃饱。梅老五私下里曾吐露出想辞工另找门户的话儿来。这事儿被邓韶清知道以后很是气忿,他决定给这个老光棍奉上一盘辣味儿尝尝。秋后,正打算结清工钱的梅老五却被县里来的公差绳捆索绑押到城里去了。当即,世面上风传梅老五私下里奸污东家的二儿媳妇。因为他侮辱秀才门面,败坏乡间风俗,才被邓韶清告到县衙里去。正在乡下组织农民协会的窦宜敏,听到这事儿以后,决定站出来维护农民的利益跟劣绅对簿公堂。就在县太爷开堂审问的当天,窦宜敏作为被告的亲属出现在大堂上。那个被充当受害人的邓韶清家的二儿媳妇对膝大跪在堂前,脸面贴着地面,羞得不敢抬头看人,嘴里却像背诵诗文似的叙说梅老五的罪行:……前后半年多光景,他就欺侮我十几次。“
哪你为什么不来县衙告发?
奴家身小力薄,怕就怕他行凶杀人,只好……说时悲声痛哭起来。堂上听众无不痛恨梅老五的恶行。
邓韶清作为受害人家长立即补充说:恶人梅老五面善心毒,他为了能长期霸占良家妇女,曾暗中准备一把钢刀,寻机杀害我全家。说到这里他把事先准备好的刀片奉上堂前作证。
县太爷怒不可遏,大喝一声:混账东西!先将梅老五棍杖四十!
窦宜敏即刻上前阻止说慢。请问大人,自古来拿贼拿脏,捉奸捉双,这件案子是否有第三者作证?
邓韶清从来没有想到窦宜敏能在县大堂上为一个小小的长工辩护。他原以为事先写好呈子,连同二百块大洋一起送到县太爷手上后,说只要在大堂上,能让梅老五认罪,并写下愿意在邓家无偿扛活八年以抵罪责的字据,再按下他的指印便大功告成。
听到窦宜敏的驳问后,他并不慌忙,立马据理力争:诗书门第从来是善良仁慈的地方,外人不能随便出入,所以发现者只有老朽。
窦宜敏继续发向:自然受害者不止一次与歹人接触,应该能揭发出歹人身上有别于常人的印记来吧。
女人说:只知道歹人体大身壮,别无特殊之处。
窦宜敏再问:你与歹人接触能否记得他身上有特殊气味?
女人说:与常人相同,并无异味。
当下,窦宜敏要求说:请清官大人在歹人身上细察、细闻,以事实证明是否有真伪虚假。
由于窦宜敏的要求在理,县太爷只好令下属于众目睽睽之中细查一番后,据实禀告:该人小腹生长肉瘤一颗,足有婴儿拳头大小。同时,该人身上具有浓烈狐臭气味,闻之刺鼻难忍。
…………
两天后,梅老五被无罪释放。
从此,窦宜敏不畏邪恶,敢为穷人伸张正义之举在乡间传开,大长了穷苦人志气,大灭了土豪劣绅的威风。邓韶清则恼羞发呆,憋在家中足足两个多月没有露世。而后,蓬勃兴起的农会在窦宜敏带领下,上门来当众揭露他剝削佃户的罪行,清算了他克扣长工、短工的钱款并当面归还。邓韶清只能一边咬牙忍受,一边暗中盘算反攻倒算的计谋。
今天,他遇上这个天赐良机,绝不肯轻易丢下。
两股团丁被相继派出去以后,邓韶清先从庆丰居叫来一桌酒菜,与李向成杯对杯,喝得酩酊大醉后便歪在坐椅子上昏睡起来。
鸡唱三遍,东方发白。分别被派到一南一北两股埋伏下来的团丁苦熬苦等半宿,一个个像晕头鸭子似的回到团防局里。李向成听罢团丁回报,遂举起桌面上盛有鸡魚的细瓷碗照地面上猛地一摔,气极败坏地反问:邓大人,这就是你的神机妙算吗?
邓韶清连忙摇着双手说:团总息怒,二百人的鞋袜一时就送到。
窦宜坤按照窦宜敏指给的线路,带人从南寨墙翻过去,边着寨墙根走到西门外。他让众人蹲在路边暗影处,自已一人顺大道径直朝火车站走去。往日里,这条路不时有巡查的团丁走过,今天却空无一人。窦宜坤一边走一边机警地察看两侧确无异样响动后,便用嘴巴唱出布谷鸟的叫声,听到传递的安全信号后,后面的人便紧紧跟上来。一行人来到火车站路口,沿路基向北,在搬道叉工人的灯影下飞快跨过铁轨,像出笼的鸟儿一样,飞向西山下的村庄。